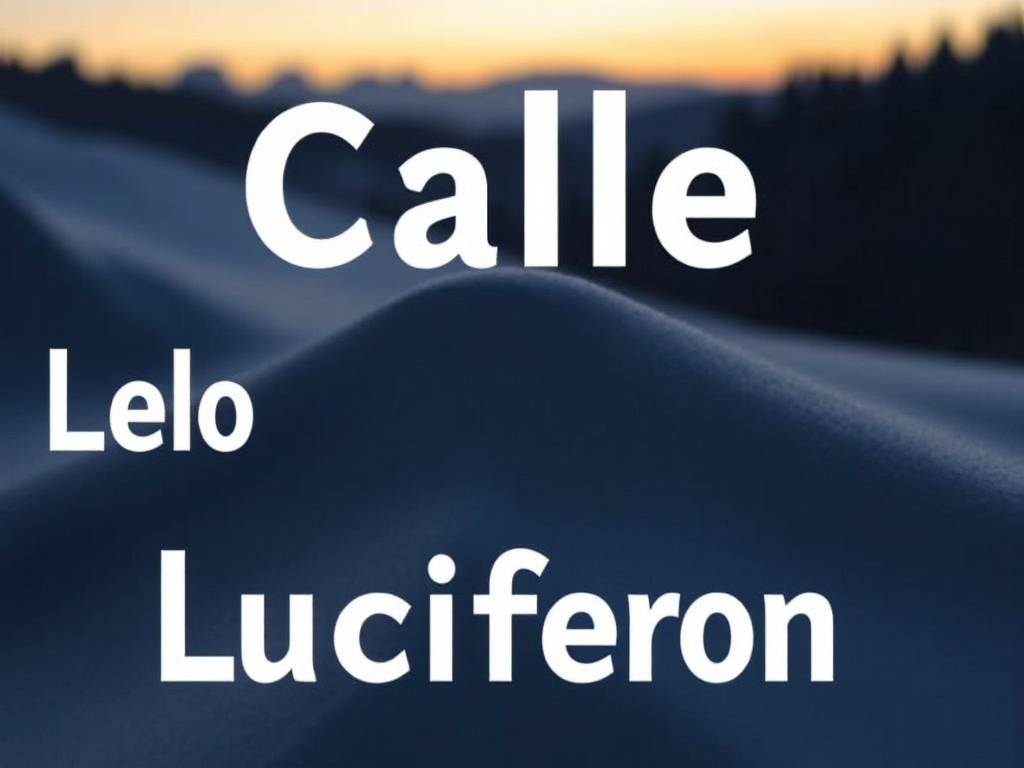姚明在美國(guó)打篮球,美國(guó)人叫他YaoMing不是MingYao,孙继海踢世界杯,外國(guó)人知道叫他SunJihai,不是JihaiSun。我依样画葫芦,以后给外國(guó)人通信都(dōu)报称LawWaiming(对,那是港英殖民时代官定港式译法,不是內(nèi)地译的LuoWeiming),很有民族快感,但不认识的人回信,仍然(rán)叫我,Hi,Mr.Waiming。又要解释半天。
汉字(zì)罗马化的努力之一(yī),坚持中國(guó)人名英译(还是拉丁译?)时还是依旧姓氏先行,真是合乎传統(tǒng),发扬尊严,都(dōu)甚得我心,不然(rán)我也不会跟风模仿,不过全球化了这么久,外國(guó)仍然(rán)有人搞不懂,我也有点无所适从。
日本朋友就没有这个麻烦,他们乖(guāi)乖(guāi)地把英译的姓氏放在名后,統(tǒng)一(yī)执行,大家都(dōu)少了许多误会。虽然(rán)主张民族尊严的人都(dōu)觉得不应该,包括认识的一(yī)些外國(guó)朋友,还在旁边怂恿改正,以复民族己观。但我至今未见过有日本人这样做。不知道这是否又佐证了中日在西化问题上的两种態(tài)度?日本人对西化规矩照单全收,中國(guó)仍然(rán)走张之洞?但细心想想又未必是。姓名外國(guó)化,日本就跟不上中國(guó),日本人鲜有英文名,流行偶像,Kimura(木村)就是Kimura,Ayumi(步)就是Ayumi,但海峡两岸與(yǔ)香港,香港不用说,內(nèi)地也开始多了很多Peter,PaulandMary……我因为不用英文名,拍《十九岁的地图》和《龙在中國(guó)》的MitsuoYanagimachi(柳町光男)拍他的香港纪录片时还追问因由,以为和民族尊严有关,当然(rán)我的答案肯定令他失望。
西风东渐,少年心性,改英文名是个潮流(有很多还是学校逼的),我又怎会落于人后,而且一(yī)不做二不休,先后改了两个,各自用了不到一(yī)个月,觉得不称心,又想改第三个,朋友当我烦,不理我,就只叫我Waiming至今。
把名字(zì)连到民族主义,当然(rán)是意识形(xíng)態(tài)想法。意识形(xíng)態(tài)理论101,就是凡事都(dōu)有意识形(xíng)態(tài)性。姓名外语化绝对是东方主义好题材。但后现代主义消费社会,商品是惟一(yī)的意识形(xíng)態(tài),名字(zì)作为一(yī)种消费,只求方便好用,在乎意识形(xíng)態(tài)会令生活紧张,不是后现代態(tài)度。
不过,中國(guó)处理外國(guó)名字(zì)的態(tài)度,肯定自我中心已经毋庸置疑,除了对待拉丁语系的人外,对汉语系也一(yī)视同仁。任何文章碰到欧美非等地人名,给他译个中文名就算,原文通常不附,有心人想继续追查,除了相传好几代大名鼎鼎的几个,即使香港、台湾與(yǔ)內(nèi)地译法不一(yī),还有迹可寻,陌生的就仿如隔路,他日别处相逢,都(dōu)不知道自己原来见过中文的他(她),只是不知道是原文的他(她)。至于汉字(zì)人名,就不管对方根(gēn)本不是中國(guó)人,汉字(zì)的发音意思用法和中國(guó)有出入,仍然(rán)只用中文发音来称呼他(她),结果到有一(yī)日面对面见到对方,才发觉叫不出人家名字(zì)。有时都(dōu)颇失礼。 ()
叫惯自己罗维明,讲英文时要叫WaimingLaw总是不习惯,所以國(guó)粹主义式的姓名拉丁化,我都(dōu)几接受。姚明和孙继海再努力一(yī)下,要外國(guó)明白,应该指日可待。不过推己及人,我们也要还原外人的原音原字(zì),方便我们对他的认识。给中译人地加注原来写法,给外國(guó)汉字(zì)加注发音,都(dōu)是应该做的事。


 微信扫一扫打赏
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
支付宝扫一扫打赏